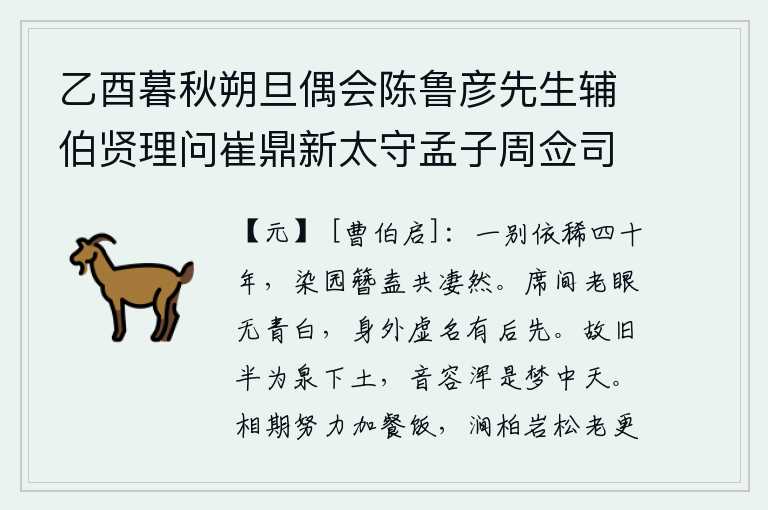
一别已近四十年,染园簪为什么要一起凄然伤感呢?
在宴席上老眼昏花,不分青白;身外虚名,却有前有后。
老朋友多半都成了泉下的泥土,他们的音信和容貌全是梦中的天。
我们相约在山涧边的柏树和岩石上的松树上,等到老了,它们的枝干更加坚实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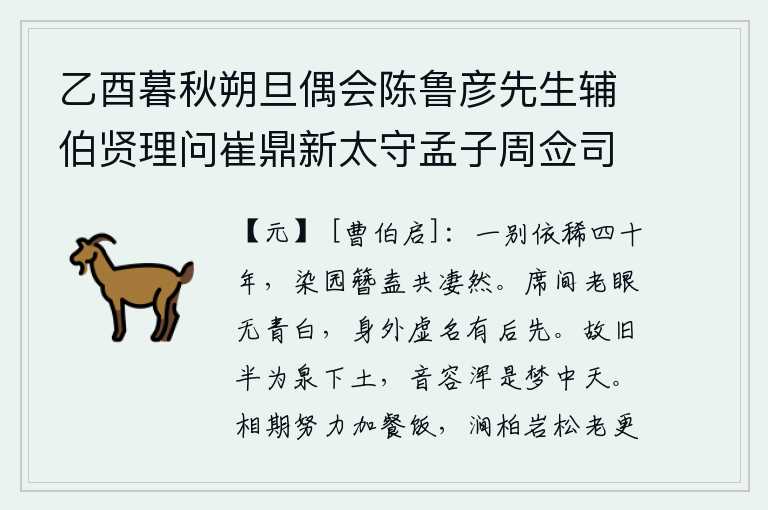
一别已近四十年,染园簪为什么要一起凄然伤感呢?
在宴席上老眼昏花,不分青白;身外虚名,却有前有后。
老朋友多半都成了泉下的泥土,他们的音信和容貌全是梦中的天。
我们相约在山涧边的柏树和岩石上的松树上,等到老了,它们的枝干更加坚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