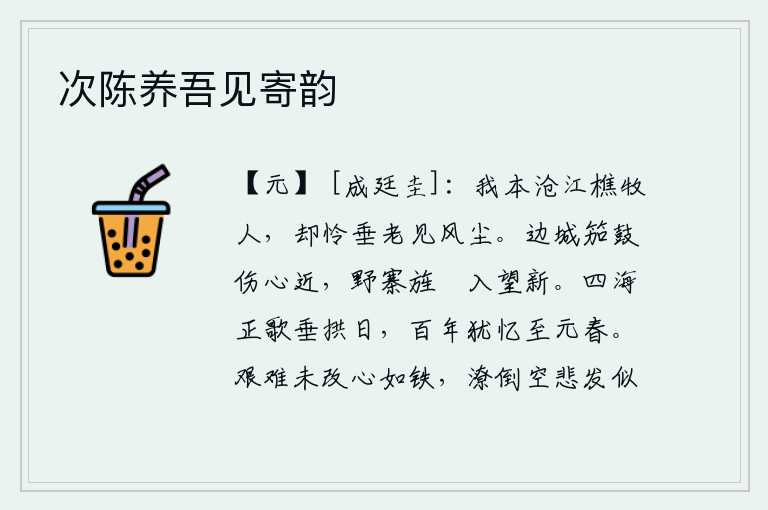
我本来是沧江一带打柴放牧的隐士,可惜到了老年却只能见到满眼的风尘。
边城的笳鼓声令人伤心,野外营寨的旗帜和旌旗一进入就觉得崭新。
普天之下,人们都在高歌欢迎皇帝的垂衣拱手之日,百年过去了,人们还怀念到元旦那一天。
在艰难困苦中,我的心仍然像坚硬的铁一样坚定不移;生活窘迫潦倒,只能白白地悲伤,头发也变白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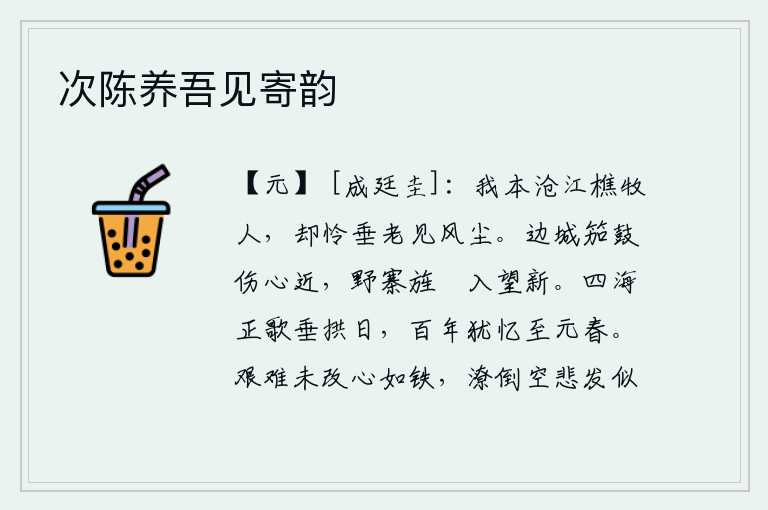
我本来是沧江一带打柴放牧的隐士,可惜到了老年却只能见到满眼的风尘。
边城的笳鼓声令人伤心,野外营寨的旗帜和旌旗一进入就觉得崭新。
普天之下,人们都在高歌欢迎皇帝的垂衣拱手之日,百年过去了,人们还怀念到元旦那一天。
在艰难困苦中,我的心仍然像坚硬的铁一样坚定不移;生活窘迫潦倒,只能白白地悲伤,头发也变白了。